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 读后感
尼尔*弗格森的作品 *Civilization* 出版于2011年。其时美国刚从Great Financial Crisis 的打击中回血,欧洲大陆还在债务危机的泥潭中挣扎。东方的中国则借力WTO的市场准入和庞大的人口红利,在烈火烹油房地产加持下高歌猛进。**一时间“北京共识”呼声高涨,而“华盛顿共识”则星光暗淡。**
Ian Bremmer 在 《The End of the Free Market》 中写道:2009年5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在纽约的一个座谈会上问他 “Now the free market has failed.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proper role for the State in the economy?”
文明》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了。 开篇作者提出一个问题:西方文明是如何在过去500年间称霸世界的? 如果有人乘坐时间机器回到十五世纪初, 那么东方的文明毫无疑问是优越领先的:远东的中心北京正兴建紫禁城;在近东,奥斯曼土耳其人正进逼君士坦丁堡。而英格兰还没有从黑死病中恢复元气,伦敦的街道上也到处铺满了“人造黄金”。那么西欧文明凭什么胜过外表看来比它优越的东方帝国,以至于称霸世界500年?弗格森认为答案是西方发展出六大“杀手级应用”:竞争、科学、财產权、医学、消费社会与工作伦理。全书以浅显易懂的文字分别讨论了上述六个因素。科学、医学,与新教工作伦理是华人读者熟知的西方成功要素,很多社会历史学家也提出过: 比如Max Weber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Jared Diamond 的《枪炮、病菌与钢铁》等等。 另外三个要素竞争、财產权与消费社会相对提及较少,但在弗格森看来至关重要。
一. 竞争。
本章讨论的是14世纪以来中国为代表的远东为何不可避免的落后于西方。 作者对比了处于相对静止之中的中国和处于政治割据分裂的欧洲。在弗格森看来,在欧洲的政治集团彼此为了香料无情的竞争之时,中国紫禁城却是平静无波与停滞不前。而竞争带来了三个好处,首先是推动了军事技术的革新, 如陆军的炮兵战术,棱堡防御,海军的新型舰艇如葡萄牙轻型多桅战船。军事技术的创新为西方赢得东西方的竞争提供了武力保障。其次竞争推动了金融创新, 如政府公债。金融创新为西方文明赢得东西方的竞争提供了财政支持。第三个好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欧洲的政治割据局面使得欧洲不能形成和中国类似的帝国。在公国之间、国内的城市之内,存在的多层级的竞争。没有一个统治集团拥有绝对的政治权利,也就没有人能做出灾难性的决定, 比如禁海。
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一章: 竞争导致创新, 创新带来优势。
二. 科学革命
本章的参照系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穆斯林世界从自从7世纪后阿拉伯沙漠崛起以后, 一直是基督徒世界的竞争者。在中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穆斯林国家的科技领先于西方世界,以至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各国需要到穆斯林典籍中学习 。与中国的静止和缺乏竞争不同, 奥斯曼帝国统治的领土上内部和外部竞争并不缺乏,帝国也积极的参与全球贸易。那么奥斯曼帝国是如何逐渐的丧失优势的呢?在弗格森看来, 没有什么比十六世纪Taqi ad-Din在伊斯坦堡塔主持修建的天文台的命运更能说明问题的了。这座当时一流的天文台在高级宗教人员的干涉下被苏丹下令拆除, 宣告伊斯兰世界科技发展开始陷入黑暗时代,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传统上认为奥斯曼的衰落始于1683年第二次围攻维也纳的失败,而我个人认为衰落的种子在1579年就种下了。此后直到1868年前,伊斯坦布尔没有建成第二座天文台。通过这类阻止研究自然科学的措施,伊斯兰教士事实上掐灭了奥斯曼科技发展的火花;而同一时期,欧洲的基督教堂却在逐步放松对自由探究精神的压制。活字印刷术(注意, 是古登堡的铅活字,不是毕升的泥活字)在欧洲和奥斯曼的不同命运也很能说明问题。 1515年,苏丹塞利姆一世颁布法令:一旦发现有人使用印刷机,他们将面临被处死的危险。这与科技进步格格不入。 没有印刷厂, 就不能推进广泛的教育。而天才的产生是随机过程,受教育的人口越多,就越有可能产生天才。假以时日,东西方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用一句话来总结这一章: 思想禁锢束缚科技的发展, 而科技的落后导致竞争的失败。
三.财产权
弗格森在这一章中对比的是南美和北美的截然不同的发展途径和结果, 讲的是西方文明内部两个流派在新大陆的竞争:北美洲输入英国文化,南美洲输入西班牙文化。通过这个对比,弗格森把前述两个因素排除在外, 因为双方(英系美洲和西班牙美洲)都是竞争和科学革命的积极参与者。作者认为使北美胜出的根本原因是其施政理念:代议制立宪政府确保个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保护私有财产的安全。这种理念远超范范的民主的范畴,并不是有个选举便自动达标。或者说民主选举只是大厦的拱顶石,而大厦的根基则是法治。此外,财富(土地)的分布同样造成了深远影响。 同样是殖民地独立,北美实现了土地的广泛拥有,而南美洲这边西班牙国王拥有所有土地,连直接参与南美革命的英国志愿军都没有得到土地。直到今天,南美的土地也是集中在少数精英的手中。这种制度的差异在接下来的400年中manifest itself:
“新成立的独立国家从一开始便没有代议制的传统,有的只是极为不公平的土地分配制度,以及因经济不均等而造成的种族裂痕。结果,在无产者努力争取更多的几亩土地,而混血精英又死抱着庄园不放手的过程中,革命和反革命、政变和反政变便交替上演。”
四.现代医学
离开南美,弗格森把眼光转向了非洲, 在那里现代医学为欧洲人殖民开发非洲立下汗马功劳。如果对付不了黄热病和疟疾,甭管欧洲人的军事力量如何发达,他们也无法殖民非洲。 其实在我看来,现代医学是科技进步的一部分, 毕竟如果没有显微镜,现代医学和细菌的斗争也无从谈起。在这一章中,作者以大量篇幅描述了欧洲各国殖民政策的区别,尤其是德国和法国的对比。德国的种族灭绝传统,原来是在非洲(今天的纳米比亚)就成型的, 只不过是到了希特勒手中应用到犹太人和东欧人身上;德国的殖民化理论家提出对于“不好的、文化上笨拙的、掠夺成性的部落”有必要进行真正的灭绝”。德国的Lieutenant-General Lothar von Trotha来到德属西南非,毫不犹豫的将此理论付诸实践。 除却在战场上的杀戮,德国的集中营也是臭名昭著的死亡营。其中Shark Island的死亡率高达惊人的80%, 这个比例已经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相去不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国的殖民政策。 法国人在1848年就在整个法帝国废除奴隶制,包括西非殖民地塞内加尔。与此同时,法国人鼓励(至少是不反对)通婚,在殖民地建立学校, 并在19世纪末期建立国家健保机构(尽管没有多少资金)。而出生于奴隶市场的布莱兹·迪阿涅也在1914年成为了第一个法国国民大会的黑人成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克莱蒙梭和迪阿涅达成协议:殖民地黑人帮忙打仗,战后给予法国公民权。今天法国巴黎的黑人区,原来缘起于此。
很有意思的是, 弗格森在书中似乎不经意的把全球变暖学与种族主义理论作了对比:
> A Crucial point to note is that a hundred years ago work like Galton’s was at the cutting edge of science. Racism was not some backward-looking reactionary ideology; the scientifically uneducated embraced it as enthusiastically as people today accept the theory of man-made global warming.
(Page 177)
五. 消费主义
如果说包括现代医学在内的技术革命是西方文明过去500年间胜出的硬实力基础,那么消费主义和工作伦理则是西方文明的软实力内核。消费主义的核心在于创造需求,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以棉纺织品为开端,涌现出大量提高生产力的技术,同时对物美价廉的商品的需求也为之扩大。在此过程中资本家们意识到如果把工人的工资压低到最低标准(比如奴隶制)其实对他们自己并没有好处。马克思的理论之所以失败,部分原因就“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大大的提高了。弗格森花了大量的篇幅讨论了以牛仔裤为代表的服装在西方消费文化中的核心地位, 讨论了从一战前的日本到冷战中的东欧对这些服饰的追求及其代表的文化软实力输出。很有意思的是, 到今天伊朗德黑兰的女大学生还在为了服饰付出生命代价,而中国的土地上不伦不类的汉服也在复兴,这是在预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走向吗?
六. 工作伦理
“新教伦理”这个概念最早由马克思韦伯在其鸿篇巨作“*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最早提出,并为学界广泛接受。历史经验也印证了这一论断。在宗教改革后欧洲的新教国家明显的比天主教国家发展更快,以至于到1700年在人均收入方面明显赶超了后者。到1940年,天主教国家的人民平均要比新教国家的人贫穷40%。从20世纪50年代起,以前的新教徒殖民地在经济上也比天主教殖民地发展得更好。然而,正如韦伯所说: Economic Dynamism was an unintended consequence of protestant reformation, 重要的是工作伦理, 新教的道德世界恰好符合这样的伦理,从而为资本主义提供了“sober, conscious, and usually capable worker。**在大部分历史中,人们为了活着而工作;而新教徒们则为了工作而活着**。既然如此,不信仰新教的国家有没有可能维持高水准的工作伦理呢?东亚的经济腾飞似乎提供了例证。
结语
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之间,弗格森写下了《文明》一书。在我看来,书中列举的西方文明的六大杀手级应用,不但为历史提供了一个解释,更重要的是为 **未来世界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预测模型。**
假定这个模型是正确,那么今天东(中国)西(美国)方之间的竞争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在回到2011年, 中国的上升似乎势不可挡:
· 竞争:中国的经济充满活力和竞争;中国的政治有走向多头共治的迹象
· 科技:中国的科技投资仅次于美国,专利授权2004年超过英国,2006年超过法国,在某些领域(如新能源)甚至是领先全球。
· 财产权:2007年中国人大通过了《物权法》,尊重私有财产
· 消费: 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家庭有着强大消费能力。2011年中国的汽车销售量1800万量,而美国受金融危机影响,汽车销售只有1200万辆。
· 工作伦理:2011年美国人每年平均工作1700小时,德国人平均工作1400小时,而中国香港平均工作超过2000个小时(具体数据有争论,但趋势毫无疑问)。
正因为如此, 北京的自信与日俱增。这一趋势在2017年川普访华的时候达到顶峰:
> 在宴会上,时任总理李克强说: “中国已拥有工业与科技基础,不再需要美国,美国对不公平贸易与经济做法的关切是无的放矢”… “美国在未来全球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应该是为中国提供原材料、农产品与能源,让中国生产高科技的工业产品与消费品” ( Battlegrounds: The Fight to Defend the Free World, by H.R. McMaster)。
时间快进到2024年, 我们回头再看上述杀手级应用,情况已经非常不同。感谢上帝,2012年给中国送来了习近平,2016年给美国送来川普。
站在2011年的弗格森, 他说:
“西方真正的威胁并非来自中国、伊斯兰或者是二氧化碳的排放,而是我们对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文明丧失了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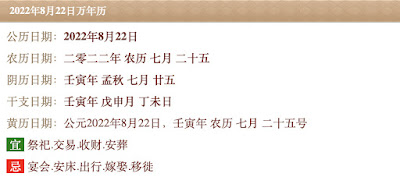
Comments
Post a Comment